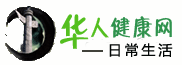青衫红袖
这年米卢吧中国足球踢进了世界杯。
长衫不爱足球,但爱抽烟。长衫喜欢抽一种叫茶花的牌子烟,有淡淡的茶香。长衫习惯在蓝色氤氲里沉思,把头深深的埋进膝盖。在地上积了一层散漫琐碎的烟灰和一根轻笼曼纱的烟蒂之后,拍拍双手,大踏步离开。
洒脱而随意。
秋天,法桐在黄昏里婆娑生姿,摇曳一身的辉煌,沙沙作响,似少女裙摆的吊钻。
闪亮而有厚度的质感。
长衫手握一支长箫,伴着翩翩起舞的落叶,把黄昏吹进五彩斑斓的边缘。
长衫把十二色的颜料混成P色,用长箫作笔,在黑白底片上署名。
长衫。
红袖蹑手蹑脚的走过来,轻轻摘下长衫的墨镜。
你为什么总是吹最凄惨最悲情的歌赋呢?
那是因为我想还世界真实。
不,你错了!世界并不如你所说的那样。
可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啊!
那是因为你戴着这副可恶的墨镜。你把它取下来,世界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了!
从此,长衫不再孤单,因为有了红袖。茕茕孑立的法桐也多了两个活泼可爱的伙伴。
每个黄昏来临之际,红袖都会采来大把大把的野花,然后依偎在长衫温暖的怀抱,听长衫那悠远而绵长的箫音。一起看恢弘的落日隐遁地平线。
每一个清晨来临之际,长衫都会把箫声吹得最柔最远,然后凝望着红袖泪光点点的双眸,嗅着红袖那来自异性特有的体香和着野花的浓烈。一起看壮丽的红日争脱地平线。
露水儿滋润黄莺甜美的鸣唱,含羞草涨红了脸把头低下。
长衫一曲一曲的吹着箫赋,双眉紧锁,那么投入,那么专注,似乎像让每一个音符都圆润、清脆、且充满灵异。红袖全神贯注,那么细致,那么向往,似乎执意想听清楚五线谱上每一个音符跳动的脉搏。
然而这五线谱上走动的哪里又是简简单单的音符呢!分明是两颗年轻鲜活的心在悸动啊!
红袖生日这天,长衫在法桐的虬枝上挂满红烛,星星点点,银光璀璨,美得像罗马的古市、埃及的宫殿。各式各样的彩灯星罗密布。大大的展开的横幅,上书:长衫永远离不开红袖!
这晚,红袖哭了,是高兴的哭,感动的哭,哭得泪流满面。泪水冰花却手舞足蹈。红袖望这长衫那放射出熠熠神采的双眼,噗嗤一声笑了。她轻轻的走至横幅跟前,将“不”换到“离”的前面。长衫使劲的点点头,仿佛要用尽一生的力气,仿佛这一点头至关重要,肩负着伟大的诺言和重大的责任。
长衫兴奋的拥着红袖跳了一支只有他们两才会明白的舞蹈。然后又坐在那快像皮垫一样松软的丑石上,为红袖吹了一支只有生日才吹的歌。
就这样,红袖爱上了长衫。
长衫开始和红袖闪电般的恋爱了。他们的关系像冬天里的火苗,干材烈火,顺风而起,见势而旺。
日子在甜甜蜜蜜中度过。
然而有一天,世界变了,全变了。
这天,长衫依旧坐在那快丑石上,吹着曲。红袖依偎在长衫温暖的怀抱,满是新奇的看着这个幸福的世界。
突然,一阵凉风掠过,尘土飞扬。蒙尘中落下一物件,长衫静静的注视着它停止了箫声。红袖迅速的跑过去,想瞧个究竟。
是丝绸吧?
不,它是一件上好的衣服。
没错,那是古司马的青衫。
它看上去很华贵,而且肃目。
红袖庄重的捧起青衫,晶莹的泪滴滚落在上面,打湿了蒙尘,并粘出鲜艳。
长衫想起有个叫贾宝玉的男人曾经说过女人是水做的,叫三毛的女人也这样说了。看来确实有点道理,因为这根本不值得感动。
红袖仿佛听到了得得的蹄音,扬起一路黄尘,奔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市井古道。故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。而她此时就坐在那片彪悍威武的枣红马上,周遭是许许多多艳羡的目光,人们惊羡她的美丽,一如惊羡她的马。
长衫扬起长箫,将一段悠扬吹得曲高和寡。
红袖捧这那件青衫,青衫需要红袖来陪衬,红袖也只有续在青衫的后面,才能彰显生命的光彩。
长衫无语,继续他的箫音。
一滴浊泪滑过长衫的鼻翼,轻巧的打在长箫的一个音口。
箫声变得暗哑而沉闷,回肠荡气。鹧鸪站在高坟上啼血,乌鸦一声剪破雾霭阒寂。法桐跌下最后一片落叶。
红袖走了,捧着她的青衫。
陈明唱过《等你爱我》;余杰写了《等你敲门》。
长衫说,他会一直在这里等红袖归来。
中国足球步入世界杯的大门,还没有真正的登堂入室,又被一记惨痛的踢了回来。
2.
这年,台湾大选。
陈水扁凭这那句“希望最美,有梦相随”在台北作竞选演说。
长衫操起拖鞋,扔了过去,并破口大骂陈水扁的那句简直可以参评本年度最晦气的竞选口号。这位台湾政要难道就不懂得已经是“不知魂已断,空有梦相随”了吗!
香港回归了,大英帝国都投降了。你台湾一个小小的孤岛又能翻出什么浪花呢!
然而这些都不关长衫的事。
无论世界怎么变化,长衫依然坐在法桐下的丑石上,吹他的箫,静静等待他的红袖归来。
法桐是一种反季节植物,长衫一直这样认为。
因为,在夏天它会穿上一身又浓又密的戎装;而冬天却一丝不挂,脱得赤裸裸的。
长衫想,这法桐真不害臊。
直到有一天,当他走进远处的一片林子。才发现,原来这个世界上不只有法桐,而且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树木和法桐一样反季节,一样不害臊。
长衫依旧每天都去法桐下的丑石上吹箫。只是有一件事他始终不明白,那就是陈水扁竟然凭这那句最晦气的口号,竞选成功了。
红袖毅然追随司马青衫远游,她们不是骑着高头枣红马,而是钻进舒适的奥迪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,一年一年的过去了。正如爱默森在《DAYS》里所预料的那样,一切都显得追悔莫及。
应该把箫声继续下去,长衫这样想,无论世界怎样变化。
在法桐换了几身衣服之后,长衫想,法桐的衣服总是那么几件,格调不及英格兰的呢裙,色彩赶不上印度的棉麻,可它却愿意穿。
月亮落下去,又升了上来。虽然张小娴曾经说过那是长脚乌龟的缘故,但它一样不厌其烦,每天固守一个轮回。
花儿谢了,总会有凯的时候。
长衫想他会等待花开的那一天的。他要看到风过群山,花开满山正烂漫。
3.
这年,连宋访问大陆,阿扁意外的送上祝福。
这年,火箭梦断达拉斯,小牛成为历史上继胡人、火箭之后,第三支在主场连败两局又扳回的球队。
长衫也终于等来守得云开见日时。
红袖回来了,一身旗袍剔出玲珑身材,款款细步,盈盈浅笑。所过之处,留影遗香,蝶飞蛾舞。
长衫依然坐在法桐下的丑石上,用陈旧的箫声迎接红袖归来。但悠远而绵长的箫音,此刻听来似另类的花殇。
古老而倔强。
一曲终了,长衫起步离开。
洒脱而随意。
而箫声依旧在山谷里久久回荡。像老人们慈祥的面容,宽容一切的弥勒佛肥硕的耳朵和厚厚的嘴唇。
红袖急匆匆的赶来。然而她没有见到长衫。长衫已经走了,只有尚存余温的丑石和千转百肠的箫音告诉她:长衫曾经一直都默默的守侯在这里,为她吹那最远最柔的箫音。
红袖大声的呼唤长衫的名字,然而没有回音,连山谷都不再回声。法桐傲然的仰望苍窘,又似一位看破红尘的禅师。现在,只愿静坐。
长衫决定离开这儿,离开可爱的丑石,离开和蔼的法桐。长衫要携着这支长箫远渡重洋,到大洋彼岸的国度——斯里兰卡,追寻他的天籁。在那里把箫音发挥到极致的纯青。
长衫原本打算去布拉格,因为那儿曾经住着上帝的逆子卡夫卡。可是人们告诉他那儿也是昆德拉的故乡,于是他决定改去斯里兰卡。
今天长衫就要乘上这次航班远行,在离开前,他要好好看看这片他所熟悉的土地,并作最后一次仰视,且奉上他最神圣的注目礼。
然而,匪夷所思的是他看到了一株法桐。这怎么可能呢?
法桐静静的矗立在机场的入口处,枝繁叶茂,郁郁葱葱,绿的流光,青的滴翠。这里怎么能生长法桐呢?
正在这时,有一位老清洁工打这儿经过。长衫急急的叫住他:老伯,这里怎么会有法桐呢?
呵呵,小伙子,可得看清楚啊,这哪里是什么法桐,只是大陆土生土长的一棵梧桐哦……。梧桐对水和无机盐的需求都很少,生命里旺盛的很哦……,容易活的……
哦,原来是这样!
长衫迷茫的望着这株“法桐”。但此刻他更清楚的是,自己错了,从一开始就错了。原来一切都只是一场误会,阴错阳差的误会吧了。
红袖远远的就看到了长衫,当然她也看到了这株法桐,她相信这株法桐比她更能留下长衫。
红袖撕心裂肺的朝这边冲过来,并呼喊着长衫。就在这时候机室里传来了旅客登机的广播。长衫没有回头,迟疑了一下,便迈开大踏步,朝机舱走去。
洒脱而随意。
红袖在后面呼天抢地的哭喊,凄惨寒绝。
长衫从容的抽出长箫,最后一脉奏响那支熟悉的旋律。悠远而缠绵。
飞机终于起飞了,人们静静的注视着那个呼天抢地的女人,满是同情,却把耳朵贴近歌赋。似乎这个苦命的女人注定应该为这首沉醉的箫音配画。
长衫走了,携着他的长箫,飞去大洋彼岸的斯里兰卡。他把属于自己的空间全部抽空,然后一走了之。做得决绝而隐忍。
他要让斯里兰卡的废墟掩埋文明的同时,也不要漏掉他这段猥琐的记忆;让斯里兰卡的沉寂冻结繁华的同时,也要荒废它腐烂的灵魂。
来年还有一季的草长莺飞,期待樱花浪漫翩翩起舞!
(编辑:蔡旭旭)
(免 责声明:本站文章和信息来源于互联网,系网络转载,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,并不 代表 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。如转载文章涉及作品内容、版权等问题,请立 即与本网站联系,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!)
-
{tag_内容页相关信息}
频道精彩推荐
- 保健
- 健身
- 减肥
- 美容
- 整形